人人應知的公禱書歷史 第15章 洗禮、教理講授、堅信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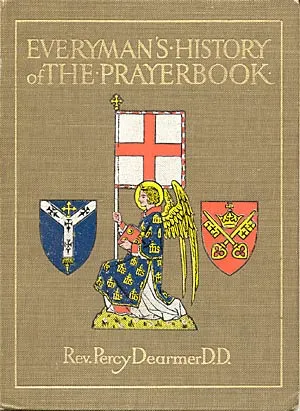
第15章 洗禮、教理講授、堅信禮
我們已經說明了四個經常使用的禮儀的歷史,包括聖餐聖禮、其序曲——連禱文/總禱文,以及日課的兩個部分:早禱和晚禱。現在讓我們轉向入門聖事。

十五世紀的格雷沙姆洗禮池的浮雕面板(身穿白罩衫/長白衣(Surplice)及聖帶的神父為嬰兒施行洗禮)。
基督徒團契的入門儀式一直由兩個部分組成:洗禮和堅信禮。在原始教會中,這兩者關係如此密切,以致按手禮只是洗禮儀式的結束部分。在東方教會中至今仍保持這種密切關係,神父在為嬰兒施洗後,立即用主教所祝聖的油膏抹嬰兒(無需按手禮)。只有在羅馬天主教會和聖公會中,因將堅信禮推遲到兒童具備理解能力的年齡,才使這完成基督徒入門儀式的聖禮與洗禮分離。在原始教會中,聖餐緊隨堅信禮之後進行;而在東方教會至今仍然如此,新受洗並完成堅信禮的嬰兒可以領受聖餐,且慣常讓幼童領受聖餐。
根據馬太福音記載,洗禮聖事是基督在其最後莊嚴的命令之一中所設立——「你們要使萬民作我的門徒,奉父、子、聖靈的名給他們施洗,凡我所吩咐你們的,都教訓他們遵守。」(太28:19-20)。堅信禮是經由使徒們所設立的,但我們毫不懷疑,他們在施行按手禮時,知道自己是在履行主的旨意。新約聖經中充滿了關於洗禮的教導,顯然作者們都視之為最高且最神聖的重要事項,是絕對必要的。從希伯來書6:2節提到「洗禮的教訓和按手之禮」,我們可以看出堅信禮也被視為基督徒生活的首要原則或基本行為之一,同時洗禮也必須以悔改和信心為先(參見使徒行傳2:38,16:31)。使徒們必定是在為信徒施洗後立即為他們按手;但是,由於洗禮可以由較低職位的聖職人員(如執事腓利)施行,而堅信禮即使在當時也是保留給教會最高職位的人員施行,我們發現有一個例子(因術士西門的事件而被記載下來),兩位使徒從耶路撒冷到撒瑪利亞,為腓利所施洗的信徒按手(使徒行傳8:5、12、14-17)。另有一個例子被保存下來,是關於使徒保羅因一次無效的洗禮而重新施洗(使徒行傳19:3-6),在這裡我們發現,正如所料,按手禮是緊接在洗禮之後進行的。然而,在聖腓利為太監施洗的例子中(使徒行傳8:36-38),並未提及堅信禮;但由於這很早就被視為(使徒行傳8:17)賜予聖靈的儀式,我們很難想像這會被省略。這個例子中的簡單信經(使徒行傳8:37)只出現在部分經文中,可能是後來加入的。
這就是新約聖經告訴我們的全部 — 悔改、信仰告白、奉父、子、聖靈之名施行的洗禮(此後一直沿用至今),以及當時稱為按手禮的堅信禮。除了與醫治病人有關的記載外,並未提及傅油禮。
使徒教父們所告訴我們的也不多。在《十二使徒遺訓》(Didachè)(可能作於主後100年,若不是更早的西元90年)中,提到了三重程式,以及事先的教導和禁食:表明偏好使用河流或溪水中的活水;若水不夠深無法浸禮,則提到在頭上傾水也足夠。殉道者游斯丁(約主後150年)在其《護教書》(Apology)中也描述了戶外施洗的情形:
“凡確信我們教義真理,並承諾按照教義生活的人,都被勸勉要祈禱、禁食,並為過往的罪悔改;我們也與他們一同祈禱和禁食。然後,我們帶領他們到有水的地方,他們就以這種方式重生,正如我們也曾經重生一樣;也就是說,他們奉全能的天父上帝、我們的救主耶穌基督,以及聖靈的名接受水洗。因為基督說:人若不重生,就不能進天國。”

上圖:亞略聖洗堂的洗禮池。
洗禮最初當然主要是為接納成年皈依者而設的儀式。在教會和平時期之後,整個四世紀期間,大量成年人放棄異教信仰並接受洗禮。到了五世紀,帝國邊緣地區的新民族開始皈依;到了六世紀,我們自己民族的皈依也開始了。因此當時仍有大量的成人受洗;在六、七世紀冗長而複雜的儀式中,這項禮儀仍然是針對成人洗禮。毫無疑問,當為嬰兒施洗時,這項儀式會失去一些感染力,正如所有曾在傳教區域見證過皈依者受洗的人都知道的那樣。但是讓基督徒的子女在基督教會內部成長,而不是作為局外人的這個原則是如此重要,以致整個基督教世界都願意放棄那感人的成人洗禮儀式,只在相對罕見的必要場合才使用。使徒們很可能為包括嬰兒在內的整個家庭施洗,因為經上提到呂底亞一家的洗禮(使徒行傳16:15),而保羅也提到(哥林多前書1:16)他為司提法那一家施洗。在第二世紀,嬰兒洗禮無疑被認為是使徒們的傳統。
大約在主后200年,特土良比游斯丁更詳盡地描述了洗禮和堅信禮,他談到這些禮儀如同早已確立且普遍實行的事物:因此可以確定,畫十字聖號、傅油禮,以及給予牛奶和蜜的習俗,甚至比這更早就存在了。特土良以其警句式的方式,概括了整個入門儀式:
肉體受洗,為使靈魂得潔淨;肉體受膏,為使靈魂得奉獻;肉體受印記,為使靈魂也得堅固;肉體因按手禮而蒙蔭庇,為使靈魂因聖靈而得光照;肉體以基督的身體和寶血得餵養,為使靈魂也得從上帝得到滋養。
根據特土良的其他著作所述,洗禮由主教主持,並經由其授權由司鐸和執事執行;但在某些情況下,平信徒也可施行洗禮。準備:候洗者必須以祈禱、守齋和守夜來準備自己。洗禮:通常在復活節前夕(夜間)或隨後的五十天內舉行。洗禮池先受祝聖;候洗者莊嚴地宣告棄絕魔鬼、魔鬼的虛榮和魔鬼的使者(在當時意味著棄絕異教儀式、異教徒的諸神和半神);然後進入洗禮池,奉聖父、聖子、聖靈之名受洗。堅信禮:主教隨後以聖油傅抹他,在他身上畫十字聖號,並按手在他身上,呼求聖靈降臨。初領聖體:特土良在同一段引文中提到這點;他在另一處還提到新受洗者會獲得牛奶和蜜(無疑是象徵他們已到達「流奶與蜜」的應許之地);我們知道新受洗者在初領聖體後立即享用這些。
我們可以想像,當這些動人的儀式在那些棄絕異教並加入教會的男女信徒身上舉行時,是何等莊嚴肅穆,而這些信徒從此將在日常生活中面臨痛苦與死亡的威脅。在異教徒被准許加入這個被社會排斥的教會之前,必須經過謹慎的考驗和教導。因此,首先,當有候選人前來時,他們的名字會被記錄下來,並對其品格進行調查,然後他們才會被接納為慕道者,每天在教會接受主教或其中一位司鐸的教導,直到復活節前夕進入教堂的洗禮池接受最後的重大儀式。當迫害時期過去,教會和平時期開始後,慕道制度被許多異教皈依者濫用,他們因對洗禮心懷敬畏而一直保持慕道者身份——直到年老或臨終時才接受洗禮。君士坦丁大帝本人就是開這個壞先例的人之一。但也有許多誠摯的人,在摸索新思想的過程中,因敬畏之心而等待,直到他們覺得自己更配得上並更有準備承擔作為基督徒的重大責任。例如,都爾的聖馬丁,出生於君士坦丁去世前後,註定要成為最睿智的主教之一,當他年輕當兵時將自己的斗篷送給乞丐時,他還只是一個慕道者。
我們知道在四世紀時,候洗者被接納為慕道者時要經過許多儀式,包括向其吹氣(驅魔),在其身上劃十字聖號,在羅馬則在其口中放置一粒鹽,在西班牙則有初步傅油禮。慕道者在大齋期間的準備包括莊嚴地來到教堂(這些「考核」在七世紀的羅馬有七次之多),每次都有驅魔和祈禱;在第三次到訪時進行「教導基督的律法」——即將四福音書放在祭台上,誦讀並解釋——以及信經和主禱文的傳授。
這種做法演變為較不正式的教理講授,持續到整個中世紀;我們現今的教會要理問答仍保留這傳統,這是一種在教會中為預備堅信禮而傳授的教導,內容包含相同的主題——信經、基督律法(十誡在要理問答中通過對上帝的責任和對鄰舍的責任而基督化),以及主禱文。教會要理問答實際上是對這三件事的精簡教導,前有洗禮誓願的教導,後附聖事的補充說明。

上圖:1689年一位神父進行教理講授。《教理講授》一書的扉頁插圖,1689年獲准出版。
因此,隨著帝國基督教化,越來越多嬰兒被接納入教會,慕道制度也改變了其性質,變成了在嬰兒受洗後,甚至常常是在堅信禮之後對孩童進行教理講授。
然而,入門儀式仍然以極其莊嚴的方式舉行,嬰兒被視同成人對待,由代理人——即教父母——代為履行其職責。因此,在我們的禮儀中,代父母所作的回應再次讓我們想起歐洲從異教轉向基督教的時期。在西方教會,七、八世紀時期的洗禮、堅信禮和初領聖體是按以下方式施行的:——
洗禮
聖周禮拜四:在彌撒結束之前要祝聖聖油,以及聖化聖油(以香膏調製的油)。信徒也會帶著小瓶子來帶一些終傅聖油以膏抹病人之用。
復活節的前一天(下午或早上)。最後的驅魔禮。以法大禮(The Effeta),即用沾有唾液的手指觸摸嘴唇和耳朵。在胸前和背部傅油。候洗者要背向西方(在東方教會中)棄絕撒旦,然後轉向東方誦念信經。祈禱後離開。
復活節前夕(守夜禮)。復活節守夜禮,期間誦讀大段大段的舊約聖經,穿插詩篇與頌歌。
主教和他的神職人員在詠唱連禱文的遊行隊伍中,手持點燃的蠟燭和香爐,前往洗禮池。(在羅馬最大的拉特朗聖約翰洗禮堂中,水池般的洗禮池中央矗立著一座紫斑石燭台,上面安放著盛有香油的金燈;池中還有基督和施洗聖約翰的銀像,中間有上帝羔羊之像,其下方是流入洗禮池的噴泉;池周圍還有七個鹿頭,噴出水柱。)當連禱文結束後,主教誦念禱文,並在水上劃十字聖號:接著兩位輔祭將點燃的蠟燭浸入水中,主教則以十字形將聖化聖油倒入水中,並用手攪拌。
候洗者隨後在兩間相鄰的更衣室內脫去衣物。由總執事引薦他們至主教面前,他們作三重信仰宣認。主教與眾司鐸和執事(全都身穿長麻布袍)與候洗者一同進入水中,將水澆在他們頭上,主教宣告:「我奉聖父、聖子、聖靈的名,給你施洗。」
堅信禮
他們前往教堂或小堂(在拉特朗聖約翰大殿,是位於洗禮堂後方的十字架小堂)進行堅信禮。主教用聖化聖油傅抹他們的頭部。在教父母的協助下,他們穿上白袍。(在高盧和凱爾特禮儀中,主教此時會束上腰帶,為新受洗者洗足。)主教呼求聖靈,並用沾有聖化聖油的拇指在每位新信徒的額頭上劃十字,對每一位說:「奉聖父、聖子、聖靈之名。願你平安。」(在東方教會,新信徒隨後轉向東方誦念主禱文。)

上圖:1520年主教為兒童施行堅信禮。(主教身穿白白色主教袍rochet、圆氅衣cope和主教冠mitre,正在為一名由跪著的代父母抱著的孩童在額頭上劃記。旁邊有一位穿著白罩衫Surplice的輔祭跪著,手持盛放聖油瓶的盤子。在祭台旁有四位穿著白罩衫和方帽的神職人員。)
初領聖體
在洗禮和堅信禮期間,詩班在教堂中詠唱連禱文。此時一隊遊行隊伍從洗禮池進入;主教在祭台前俯伏,然後站起,開始詠唱”榮歸主頌”,由此開始復活節第一台彌撒。此時仍是夜晚。在這台彌撒中,新信徒穿著白袍,站在祭台前初次領受聖體。之後他們飲用在感恩經(canon)中已祝福過的牛奶、蜜和水。(羅馬禮之中,此儀式在大聖格里高利時期被取消。但在科普特教會中仍然保留。)接著便迎來復活節的黎明。在復活節八日慶期期間,新信徒每天穿著白袍前往教堂。

十五世紀嬰兒堅信禮。(格雷沙姆洗禮池的浮雕面板。主教穿著主教白袍、兜帽,他的主教冠已經損壞。)
這些莊嚴的禮儀儘管形式多少有所簡化,至今仍保留在基督教會的不同支派中。隨著成人受洗的需求減少,而整個基督教世界中需要受洗的嬰兒數量激增,這些儀式在意義和性質上都發生了改變。禮儀舉行的時間增加了,西方教會首先加入了五旬節,東方教會則增添了主顯節和聖誕節;司鐸們起初只是協助主教,後來在主教臨場時執行這些重要場合的儀式,但堅信禮所用的油膏祝福權仍專屬於主教;其後因應需要,他們在其他聖日也可在主教不在場時施行洗禮(《公禱書》第一條洗禮規程仍將「主日及其他聖日」列為此聖事的適當時機)。在東方教會,他們也為新受洗者施行聖餐禮,主教的職責僅限於每年祝聖聖化聖油。但在西方教會,由於堅信禮仍需要主教在場,新受洗者必須等待主教巡視的機會,往往需要等候很長時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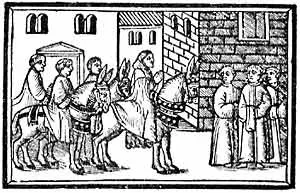
1520年主教外出巡遊。(他騎著騾子,白色主教袍rochet外披戴兜帽。三位神職人員騎騾子隨行,另有三位步行在前。)
因此,在中世紀時期,孩童往往已經長大了才等到主教巡視並為他們施行堅信禮(主教當時身穿白色主教袍和兜帽hood或无袖袍Chimere,而且常常是騎在馬上進行簡短的儀式);如此一來,嬰兒領受堅信禮和聖餐的習俗便緩慢地、逐漸地消失了。在1661年的最後一次修訂中,趁此機會將堅信禮定為孩童達到具有辨識能力的年齡時公開重申洗禮誓願的場合;但改革者原本的意圖是讓他們在領受堅信禮和初領聖體時仍然相當年幼,而且直到十九世紀,他們有時候還不到十歲,很少會超過這個年齡一兩歲。
中世紀的英格蘭,雖然保留了古羅馬教會大部分儀式的簡化形式,但也加入了一些高盧傳統,其中最著名的是向嬰兒贈送點燃蠟燭的習俗——這是一個意義深遠且富有象徵意義的行為。祝聖洗禮池已發展成為一項獨立的禮儀,在復活節大守夜和五旬節大守夜舉行,不論當時是否有嬰兒要受洗,聖水都會被更換並重新祝聖:這莊嚴的祝福禮確實是唯一一個還保留著幾分古老華貴氣象的古代儀式。洗禮本身的施行可能類似現今在意大利或法國所見到的倉促儀式,可能會更不莊重。
第一本英文《公禱書》恢復了嬰兒洗禮本身的意義,這在莎霖(Sarum)禮儀中,已經被許多早已失去大部分意義的儀式所淹沒。祝聖洗禮池仍是一項單獨的禮儀,規定每月舉行一次。禮儀的準備部分(慕道制的遺留)仍在教堂門口進行,而且中世紀時洗禮池一直放在那裡,現在法律仍要求如此;嬰兒在那裡被取名,在額頭和胸前畫十字記號,並進行驅魔。誦讀福音書後,會長和會眾誦念主禱文和信經,然後所有人前往洗禮池,繼續進行與現在相似的禮儀。洗禮之後,為孩童傅油,並為其穿上白袍(稱為chrisom,即嬰兒洗禮袍)。

薩克斯特德教堂的洗禮池。(為避免對聖水的迷信和濫用,以及為了避免異物落入洗禮池之中,13世紀左右開始,使用木質的蓋子,蓋上洗禮池。1220年达勒姆议会之中法令規定,必須加蓋枷鎖。尤其是在東英吉利,此蓋成為一個華麗的高聳的結構,當需要使用洗禮池時,通過滑輪組結構將其升起。)
在第二本《公禱書》中,祝福洗禮池的禱文(克蘭麥於1549年取自高盧莫扎拉伯彌撒書)被置於洗禮儀式之前。慕道制的遺留部分通過省略驅魔和信經,以及將劃十字記號和主禱文移至洗禮之後的現在位置而進一步簡化。禮儀改為直接在洗禮池開始,因此失去了從教堂門口的小型遊行隊伍,以及其優美的祝禱詞:“願主恩准接納你進入祂的聖家,並永遠保守引導你,使你得永生。”(The Lord vouchsafe to receive you into his holy household, and to keep and govern you aiway in the same, that you may have everlasting life.)傅油禮和白袍也被省略。在1661年的最後一次修訂中,通過加入“將水分別為聖,用以成就洗罪的奧妙聖事”這句話,使祝福洗禮池的意義更加明確,並在標題中加入“嬰兒”一詞,因為當時在《公禱書》中加入了成人洗禮的新禮儀,這使其與最早期的洗禮儀式相呼應。此時,要理問答也從堅信禮儀中分離出來,單獨刊印。
近年來出現了一種造成不小傷害的觀念:就是認為教會的每項禮儀都有一種正確恰當的執行方式,若不能按照某種想像中的標準來進行,就是對所謂大公教會規制的重大冒犯。當然,每個教會的聖品人員都有責任遵守該教會的規程並遵循其合法習俗,這是事實;同樣真實的是,當他們偏好自己的個人判斷時,就會對禮儀造成極大損害——例如在喬治亞時代,洗禮儀式最終淪落到在私人住宅的客廳中,或是在洗禮池中放置小盆為兒童施洗。但是本書前幾章至少已經清楚表明,教會的任何儀式都不存在唯一的執行方式;這一點在基督教入門儀式的兩個環節所積累的諸多變化中的禮儀和儀式上,更是明顯不過。

洗禮(出自卡利斯圖地下墓穴,二世紀)。鴿子表明這是基督受洗的場景;但在地下墓穴中也有同時期的慕道者受洗圖像,除了沒有鴿子,以及施洗者穿著長袍和外氅而非這裡的腰布外,其餘完全相同。左側是另一個洗禮的古老象徵——漁夫從海中拉出魚。